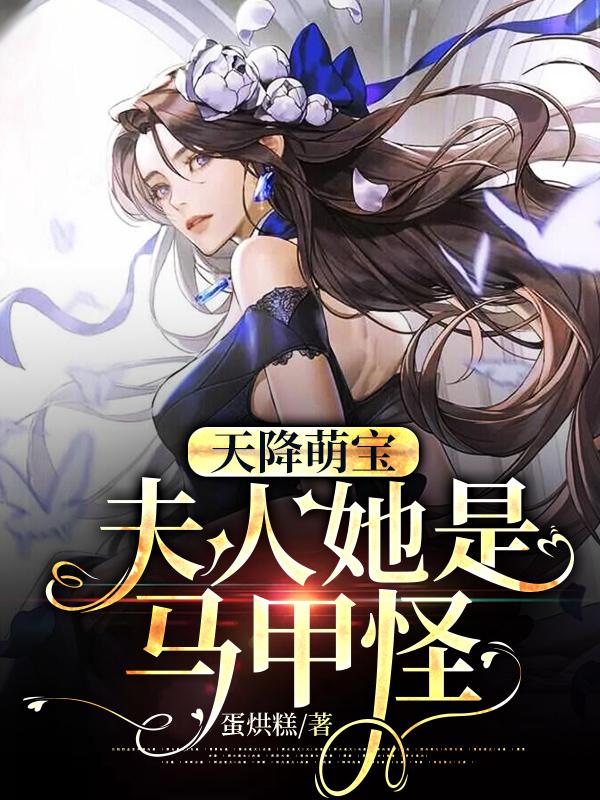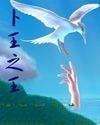笔下看书阁>大明:从监国开始卷疯全世界 > 第37章 明修栈道(第3页)
第37章 明修栈道(第3页)
朱瞻基:“………”
字可以差,情谊不能变。
——
接下来的几天,朱瞻基都在焦急等待消息。
新盐虽已制成,但销售仍是关键。
沈文度的任务便是联络各地富商,其成效直接关系到计划的成功与否。
与此同时,朱瞻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三叔的消息。
按理说,三叔应早已抵达应天,可锦衣卫的情报却显示他才刚离开山西。
若非夏原吉提醒,朱瞻基或许会怀疑三叔不愿回返,故意拖延行程。
然而,有了提醒后的他立刻否定了这种猜测。
唯一的解释便是三叔早已返回应天,只是隐藏行踪,悄然观察一切。
尽管朱瞻基已将此消息告知张懋,但由于三叔对锦衣卫了如指掌,故张懋至今仍未有任何进展。
结束一天公务后,朱瞻基回到太子府,恰遇一名锦衣卫着飞鱼服来传信,他判断要么是三叔回来了,要么是沈文度有新动态。
综合考量后,他更倾向于后者。
心中忧虑稍解,朱瞻基换上便装,来到诏狱与张懋、沈文度会合。
相较于以往,沈文度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。
因受限于规矩,他今日着装朴素,无丝毫奢华之气。
“末将叩见太孙!”
沈文度起身恭敬行礼。
朱瞻基点头示意,坐定后注视着跪地的沈文度说道:“听闻你近期表现不错,应天已有不少富商慕名而来,尤其是江南一带,商贾云集。”
沈文度深知自己的一切举动难逃皇太孙法眼,于是坦诚回应:“草民不敢居功,这一切皆得益于太孙殿下授予的锦衣卫百户令牌,方能让那些富商重视我的建议。
否则,即便我再有能力,也难以轻易说服他们。”
朱瞻基闻言轻笑一声,说道:“既然是你所为,那便承认吧。
我这地方一向赏罚有度,你既已办好我的差使,我又怎会小气于赏赐。”
说着,他瞥了眼伏跪在地、几乎将头埋进尘土中的沈文度,略作思索后开口道:“要不这样,往后你在锦衣卫挂个名号,虽非正式编制,却也算一名编外人员,权职与百户相当,专听我调遣,见了我也无需自称平民了。”
此言一出,跪伏的沈文度激动地稍稍抬起脸,试探性地问道:“殿下之意是……不再是草民,而是成了官员?”
沈文度的反应并非没有道理。
自明朝立国以来,朝廷一直推行重农轻商的策略。
甚至在衣着上也有明确规定,一旦家中有人从事商业,全家便不得使用绸缎、纱罗,只能穿绢布或棉布。
至于跻身仕途,则更是遥不可及,商人连基本的法律保护都得不到。
直到朱棣登基后,因社会环境的变化,某些抑制商业的政策才稍有放宽,但即便如此,也只是轻微调整。
各地商人为了自保,逐渐形成了如徽商、晋商、龙游商帮和洞庭商帮等团体。
听完沈文度的话,朱瞻基点头示意认可他的能力。
沈文度的能力确实令人满意,而有才能之人无论在哪都会被重视,朱瞻基自然也不例外。
因此,为了让他更加尽心尽力为自己效命,朱瞻基并不介意给予一些简单的嘉奖。
给予沈文度一个锦衣卫的编外身份不过是举手之劳。
赏赐完毕,朱瞻基便切入正题:“说说具体情况吧,我看看如今有多少富商可堪大用。”
沈万三领命,立刻答道:“属下按照太孙指示,从应天出发,经江西,入广东,再至福建,最后绕回浙江,再由浙江至山东返回应天,途经五省,七十八地,结识富商一千二百余人,其中资产超过百万银两的有五百四十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