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下看书阁>瀚海驭风 > 第96章 工人要替国家想(第2页)
第96章 工人要替国家想(第2页)
最黑暗的夜里,有全家大年三十包着有毒饺子一同寻短见的;
也有人在失控的绝望中,提刀闯进办公室,捅死了自己的领导;
还有踩着破单车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,自己晚上再默默接回来的男人,面无表情地骑在刺骨寒风中。
那些画面,一帧帧嵌进骨头里,无法挥去。
可真到了这一步,他也清楚,如果不这么做,风能公司又能撑多久?靠什么去跟那些大项目、大资金角力?光靠苦撑,连拿下Vensys许可证的钱都挤不出来,还谈什么未来?
谢世齐闭了闭眼,仿佛压下心头最后一丝犹豫,低声道:“既然你们已经定了,就放手去做吧。有困难,有压力,我给你们兜着。”
麦麦提听了,心里反而松了口气。
对他而言,这种事必须当机立断,所谓不破不立,牺牲一小部分,成全一大部分,是时代必然要走的路。
他脑海中忽然浮现起一组早已烙印在心底的数据——1993到2001年,中国共有七千万人从国企或集体企业下岗,以一家三口算,直接影响了两亿多人。
那一代人的沉默、对于体制留恋的情结,在后来的年轻人口中,常常被轻易地解读成软弱、守旧。
有人埋怨自己的父辈不够果决,说如果当年敢南下闯荡,自己说不定就是富二代。
可麦麦提明白,所谓下岗,从来不是小品里那句轻飘飘的“我不下岗谁下岗”,而是真刀真枪割向琐碎与生计,动辄粉身碎骨。
所以,与那些一纸通知、寒冬散尽的悲剧比起来,这次风能公司的“分流”,已经是极其温和的处理了。
那些人被派往外协单位,薪资待遇不降,还有机会磨砺技能,攒下资历,远比一纸下岗通知要强太多。
只是,这一刀砍下去,不管多么温柔,总归是要流血的。
马文斌则显得更加复杂。
他知道,在这场改革中,自己不得不扮演那个“恶人”的角色,要亲自去找人谈,要亲手把一张张名字划下去。
无论心里再怎么安慰自己是“是为大家好”,该面对的眼泪、怒气、不甘,一个都不会少。
他甚至能想象,有些老员工看着他的眼神,会有多锋利、多失望。
可转念一想,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
总要有人把手伸进脏水里,总要有人背负起被骂、被恨、甚至被遗忘的责任。
他抬起头,看见窗外斜斜落下的阳光,落在谢世齐深陷的眼窝里,麦麦提略微发白的侧脸上,也落在自己微微颤抖的手指上。
时间,不等人。
第一批名单筛选,在沉默中开始了。
麦麦提、文斌,还有人事部的几个骨干,关起门来,一页页翻阅档案,一行行敲定名单。每划掉一个名字,就像在心头划下一道细微但真实的伤口。
筛选的标准表面上很冷冰冰:岗位冗余度、近三年考核记录、技能匹配度、未来岗位适应性。
但真正落到个人身上,哪一条又能纯粹客观?每一份打分背后,都藏着数不清的故事。
很快,人情关系也开始渗透进来。
有领导的亲戚,托人带话进来;有老同志打着几十年功劳的旗号,委婉求情;更有的,直接堵在办公室门口,红着眼眶,一遍遍说自己:“上有老下有小,再分走就是绝路”。
麦麦提和马文斌早有准备,但真正面对那一张张熟悉又卑微的脸时,心里还是像被细细锯着。
马文斌有一次差点心软了——那是一个在水利建设时期就跟着他们的老焊工,满手老茧,嘴上说着“不想给年轻人添麻烦”,却在拐角处悄悄抹了眼泪。
麦麦提拦住了他,只说了句:“一次心软,就是对所有人不公。”
马文斌最终咬牙签下了那份名单,手指却在纸上微微发抖。
最棘手的问题,并不在名单本身。
由于深航的生产线规模有限,岗位吸纳数,比预期少了整整三分之一。
外派分流还能覆盖部分人,剩下的,却要直面真正意义上的——下岗。
这其实是麦麦提早有预感,却无法避免的事。
消息传得比想象中更快。
反抗,也在所难免。
有个年轻的维修员,听到消息,拎着上螺丝用的扳手,闯进人事办公室,拍着桌子吼:“凭什么?我才干了三年就让我滚?凭什么不是那些喝茶看报纸的老油子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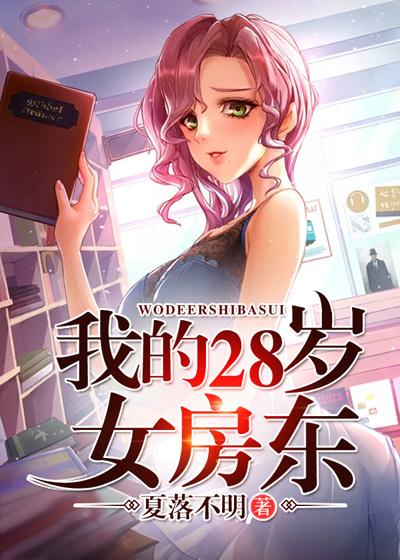
![[红楼]林氏第一神医](/img/6876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