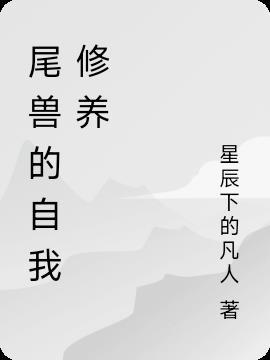笔下看书阁>踹掉渣男世子,本宫转嫁他死对头 > 第76章 自欺(第2页)
第76章 自欺(第2页)
蔡氏浑身剧颤,喉间发出“嗬嗬”声响。
卫云姝直起身,看着琏姨娘慌忙喂参汤,唇角笑意愈深:“母亲好生将养,明日诏狱提审,本宫定会替您。。。好好关照飞燕。”
阆华苑内药气弥漫,卫云姝抬眼看向榻上面色灰败的蔡氏:“说起来,母亲要我用什么身份求情?是司徒家弃若敝履的儿媳,还是临川公主?”
蔡氏猛地撑起身子,“就凭你冠着司徒家的姓!”
“这姓氏我早想还了。”卫云姝抽出和离书轻晃,“母亲若肯让司徒世子签下和离书,说不定我一高兴就想开了。”
“放肆!”茶盏擦着卫云姝鬓角飞过,碎在青砖上溅起褐渍。
她抚着耳坠轻笑:“母亲可知,飞燕妹妹私印盖的盐引,走的是国公府的漕运?”
蔡氏瞳孔骤缩,喉间涌上腥甜。
“三日前费府抄出账册时,金吾卫便盯上国公府的商队。”卫云姝将染血的盐引丢在榻前,“若非我当机立断斩了七艘货船,此刻跪在刑部的可不止司徒飞燕。”
暮鼓声里,卫云姝步出阆华苑。
秋平递上手炉:“公主何苦走这遭?”
“本宫要亲眼看着。”卫云姝抚过袖口金线牡丹,“看着她们母女,如何把司徒家百年清誉。。。一寸寸毁成齑粉。”
暮色浸透阆华苑的茜纱窗,蔡氏攥着金丝楠木佛珠的手指节发白。
从费府走了一趟回来的嬷嬷跪在青砖地上,冷汗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:“老奴亲眼见费府匾额被摘,费大爷在府门前捶胸顿足,痛骂大小姐连累他们费家。”
“胡说!”蔡氏猛然掀翻掐丝珐琅香炉,沉香灰烬扬了满室,“飞燕最是胆小,怎敢碰私盐!”
铜漏声里,司徒长恭的皂靴踏碎满地残香。
玄色披风扫过门槛时,正撞见母亲攥着嬷嬷衣襟嘶吼:“定是有人构陷!”
“母亲还要自欺到何时?”司徒长恭扯下披风扔给侍从,“大理寺从飞燕陪嫁铺子里搜出盐引,盖的是她私印!”
蔡氏踉跄着跌坐软榻,翡翠禁步摔得四分五裂。她突然抓住儿子战甲下摆:“定是卫云姝!她记恨飞燕动她嫁妆,故意下套!”
“够了!”司徒长恭额角青筋暴起,“上回飞燕登门谢罪,明明理亏在先,却非要准备动手打云姝,满院仆妇都瞧见了!”护腕铁片刮破母亲掌心,血珠渗进金线云纹。
嬷嬷抖着身子呈上密信:“费夫人带着家丁堵在西角门,说要。。。。。。要拿大小姐抵债……”
“抵债?”蔡氏抢过信笺,目眦欲裂,“费家这些年吃用我儿多少军饷!”纸笺被撕得粉碎,飘落如雪,“去!把那些白眼狼打出去!”
司徒长恭按住腰间剑柄,剑穗红缨簌簌颤动:“母亲可知私盐案牵扯多少权贵?皇亲国戚都折进去三个!”他忽然想起诏狱里妹妹溃烂的脚踝,“儿子拼着军功不要,也换不回个死囚!”
“去找卫云姝!”蔡氏突然疯魔般扯住他护心镜,“让她去求太后!太后养她十五年,总归有情分。”
司徒长恭眉头紧锁,猛然甩开母亲:“您当云姝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蠢女人?”
更漏声催,暮色愈发像是染了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