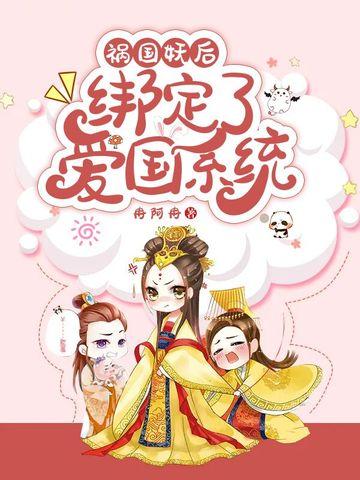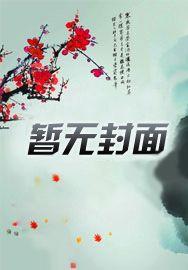笔下看书阁>唐末:从一介书生到天下共主 > 第45章 古文(第1页)
第45章 古文(第1页)
唐末文学发展脉络,李佑是大略知道的,因为专业课老师大略讲过。
将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,一共经历了两次古文运动。
此时此刻,第一次古文运动早已结束,第二次古文运动还在萌芽当中。
在两次古文运动之间,是诗赋文学的繁荣和逐渐走向形式化。
晚唐时期,朝政腐败,社会矛盾重重。包含大量异端思想的作品不断涌现,为新的文学思潮奠定基础。
随即,诗坛百花齐放,各种流派争奇斗艳,翻开了唐代文学精彩的篇章。
当时的流行文学主要是诗赋,各种应举的时文也颇为盛行。
晚唐时期,诗风逐渐走向雕琢辞藻、追求形式工整,部分诗歌内容空洞无物。
随着社会矛盾加剧,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文学现状,力求变革。
于是,新的文学思潮开始酝酿。
一些文人一边吸取诗赋文学的韵律之美,一边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实用价值。
两者之间,很难进行调和,导致晚唐部分文学作品充满华丽辞藻却缺乏实质内涵,已然走进了形式主义的误区。
文章也是如此,士子们喜欢研究秦汉古文,又不吸取秦汉古文的菁华。反而热衷于堆砌辞藻,特别喜欢用生僻华丽的字词。
僖宗初年,青黄不接,属于大唐文气最凋敝的年代!
……
船儿在颍上县石塘镇停靠,苏皓手捧《韩柳等大家文集》,已然失去访友的兴致,只想留在船上继续读文章。
“少爷,到了。”周武提醒说。
苏皓只得捧着书走,徜徉回味古文真趣,满脑子的“朝闻道,夕死足矣”。
李佑跟在身后,望着那繁忙码头,此刻目瞪口呆,心想:颍上县究竟有多少个超级大镇?
石塘镇,堪称全国首屈一指的造纸业中心。凭借着当地丰富的竹、麻资源,以及传承已久的精湛技艺,每年产出的纸张数量极为可观。
其中,有一种特制的“贡宣”,因其质地细腻、色泽莹润、墨韵层次丰富,被朝廷钦点为书写奏章和重要文书的专用纸品。
镇上的造纸工人就有上万,而此时整个颍上县,在籍人口也只有一万多。
来到镇外的豪华大宅,递上名帖之后,门子立即带他们去会客厅。
“大昭兄,哪阵风把你吹来了?”苏源走出院落迎接。
苏皓说道:“犬子童试,顺便来你这里走走。”
苏源是苏皓的族兄弟,并不出自汝阴主宗,两支的字辈都对不上。
石塘苏氏也很有实力,主要经营造纸业务,苏源的家里养了上千造纸工人。
寒暄两句,苏皓迫不及待道:“贤弟且观此书。”苏源亦颇有才名,可惜只是个秀才。他瞧了瞧封面,便摇头道:“这本书我看过,对科举文章无甚帮助。”
苏皓想了想,点头说:“确实如此。”
科举发展到晚唐,儒家经典的每个句子,都被反复考过多次,再没写出新花样。
那就只能一味求怪,越怪就越能吸引阅卷官。
能用生僻字,就坚决不写常用字。
一个字有多种写法,那就专挑复杂的来写。
而韩愈、柳宗元等大家,皆真情实性,遣词造句比较直白。这种文风很难模仿,若无深厚的功底,若无丰富的阅历,便容易写得平庸粗浅。
科举文章,最怕平庸,到晚唐,士子们干脆不读韩柳等大家之作。
准确来说,韩柳等大家,被科举淘汰了……
突然,苏皓又摇头说:“乡试如此,会试则不尽然。”
“或许吧,”苏源苦笑,“我乡试都未过,不敢模仿韩柳文风。”
全套科举流程,乡试可称最难,尤以江南、巴蜀等地难上加难!
江南、巴蜀士子,若无超卓才学,以韩柳的文风去考乡试,那无疑就是自寻死路。
全国会试则不一样,不用刻意求怪求新,能把道理讲清楚就是好文章。
苏皓负手而立:“吾当潜修韩柳等大家之作,两年之后再去京城赴考!”
“祝君金榜题名。”苏源拱手笑道。……
却说林渊走出考场,已经是下午时分。
郑知县当时不在,师爷对林渊青睐有加,但无法做主录取,只说一定帮忙推荐。
应该考过了,县试并不难,录取了也没啥用,真正难的是乡试和会试。
林渊在考场之外,找不到自己的小伙伴,便顺着颍上河走路回家,估计要走到半夜才能抵达。
一边走,一边回忆文章,林渊越想越兴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