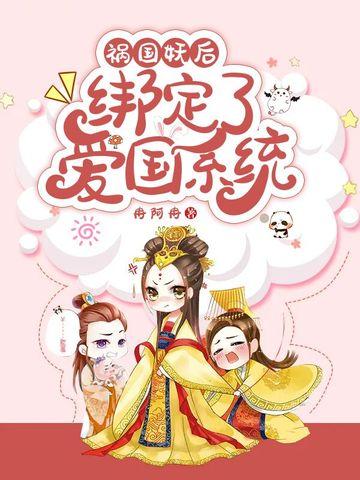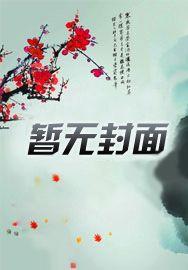笔下看书阁>唐末:从一介书生到天下共主 > 第8章 风云乍起(第1页)
第8章 风云乍起(第1页)
李佑望着紧闭的城门,心急如焚,小妹的高烧还在持续,再不找到大夫诊治,后果不堪设想。可这新郑县城,就像一座冰冷的堡垒,将他们拒之门外。
李佑在一旁看到这一幕,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。
他让小妹靠墙躺好,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衫,快步走过去,对着苏皓拱手作揖,恭敬地说道:“小子拜见先生!”
苏皓上下打量李佑一眼,疑惑道:“你是……哪位故人之子?”
“小子祖上是太宗皇帝的第16代玄孙。当年宣宗出征,先祖随驾,不幸在乱军中丧生。
家父姓李,讳少凌。”李佑神色镇定,不慌不忙地胡诌,将自己的出身拔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。
“李少凌?”苏皓拧起眉头,绞尽脑汁思索良久,随后缓缓摇了摇头,“从未听闻令尊名号。”
那自然,本就是随口编的,能听过才怪。
李佑脸上瞬间浮现出悲戚哀伤,半真半假地哭诉起来:“家父一生忠君爱国,为人刚正不阿。虽身为皇室宗亲,却因不屑于卷入朝堂纷争,远离权力中心,恪守本分,以致家境并不宽裕。
去年大水,席转而去,不知所踪。
今年郑州大旱,赤地千里,庄稼颗粒无收,家中实在难以维持生计,阿爷便带着全家踏上了逃荒之路。
哪曾想,在郑州城北,遭遇了一群悍匪。那些匪徒穷凶极恶,阿爷、母亲、他们……皆惨遭毒手,只留下我与小妹,在乱刀之下侥幸逃生……”说着,李佑眼眶泛红,声音也微微颤抖。
苏皓听后,不禁大为动容,他在郑州停留的这段时间,确实听闻城外匪患猖獗,李佑所说的情况与他了解的能对上。苏皓长叹一声,感慨道:“唉,这动荡不安的世道,竟连皇室宗亲的日子都如此艰难,真是让人唏嘘。”
李佑抬手,指着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小妹,又晃了晃手中那柄长矛,接着说道:“我带着小妹四处漂泊,一路上风餐露宿,靠着乞讨勉强活命。可谁能想到,即便是乞讨,也时常遭受其他乞丐的欺凌。
幸好父亲生前曾传授我一些武艺,在那些危急时刻,才得以护我兄妹周全。可如今南下途中,小妹突然身染重病,昏迷不醒,我心急如焚,一心想进县城找大夫为她医治,可这城门却紧紧关闭,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”
苏皓转头瞧了瞧李萱,眼中满是同情之色:“你们兄妹二人如此年幼,就经历了这般磨难,一路走到这里,其中的艰辛怕是常人难以想象。”
李佑见苏皓只是说着些不痛不痒的话,却不肯帮忙,心中一急,猛地跪地磕头:“恳请先生带我兄妹二人进城!”
一旁的周武突然帮腔道:“公子,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。”
苏皓瞪了周武一眼,这才对李佑说道:“起来吧,且在这里一起等着。”
约莫一刻钟后,新郑知县崔洋终于出现在城楼上。
苏皓笑着抱拳道:“旂召兄,许久不见,别来无恙啊。”
崔洋板着脸,没好气地说道:“苏大昭,听说你要回江西坏我名声?”
苏皓笑嘻嘻地说:“岂敢岂敢,愚兄此番前来新郑,不过是盘缠用尽,想找旂召兄借几贯铜钱做路费。”
崔洋突然破口大骂:“苏大昭你个混帐东西,老子跟江西那些人可没什么关系。你尽管回江西去造谣,老子今天还就不让你进城!”
“嘿嘿,”苏皓依旧笑着,“老弟若真不让我进城,又何必亲自登城相见?”
崔洋冷哼一声,对门卒说道:“放下吊篮,把这混帐东西拉上来!”
崔洋,字旂召,山西太原人,出自名门望族,唐僖宗乾符二年中举。
苏皓与崔洋是多年旧识,一同参加过几次科举,却都名落孙山。
崔洋不愿再考,便请托家中长辈,谋得了新郑知县一职。任职期间,他也曾想做个好官,可这世道混乱,渐渐也被官场的污浊所染。
两个吊篮从城楼缓缓放了下来,苏皓不紧不慢地跨进其中一个,还潇洒地挥着折扇,下令道:“起!”
李佑见状,不等周武进吊篮,便快步上前挡住。
李佑对着周武深深一揖,并不言语。
就这短暂的接触,李佑便看出,看似和善的苏皓,实则不太好打交道,而粗鲁的周武,却是个热心肠。
果然,面对李佑的长揖,周武没有跨进吊篮。他反手抽出熟铁棍,转身面向围过来的饥民,对李佑说:“你进去吧。”
“多谢!”李佑抱着小妹,一起坐进吊篮。
周武挥舞着熟铁棍,大声喝道:“谁敢再往前一步,就别怪我不客气!”他面相凶恶,顿时将饥民们吓退。
李佑来到城楼,连忙向知县作揖致谢,崔洋只是微微点头。
苏皓靠在城垛上,懒洋洋地俯视着城外的惨状,像是漠不关心,随口说道:“这两个孩童,是我一位故友之后。唉,全家惨死,只剩他们兄妹相依为命,麻烦老弟帮忙找个好郎中。”
崔洋不耐烦地挥挥手,对随从说:“带他们去县衙,请郎中来看病。”
“多谢两位恩公!”李佑闻言,真心实意地跪下道谢。
待兄妹二人离开,周武也被拉上城楼,苏皓突然转身,严肃地对崔洋说:“新郑县饿殍遍地,贤弟为何还派衙役下乡征收赋税?就不怕激起民变吗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