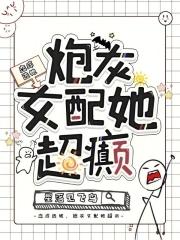笔下看书阁>大明:我在洪武当咸鱼 > 第25章 陈近南装逼跟我胡惟庸有什么关系(第2页)
第25章 陈近南装逼跟我胡惟庸有什么关系(第2页)
“依解某看来,以后胡大人的题目,恐怕会越来越刁钻,要是没有几位得力的兄长一起研究,到时候解某恐怕会束手无策啊!”
方孝儒之前一直没怎么说话,此时听解缙提到栖霞寺再聚讨论考题一事,反而来了兴致。
“如果是为了讨论考题的话,那方某倒是愿意参加!”
“胡大人的题目……虽然有些机巧之处,但确实有些离经叛道。”
“方某觉得,若还是按照以前的路子去琢磨,方某必定会落榜!”
“唉,胡大人此举,对我们这些学子太苛刻了!”
听着方孝儒在那里抱怨自己,胡惟庸只当没听见。
他清楚,对于方孝儒这种恪守传统、一丝不苟的读书人来说,说他离经叛道,已是最温和的评价了。
那些背地里不知有多少人在骂他,骂得多难听,他也无从知晓。
但胡惟庸并不在意。
你们爱骂就骂吧,难道老爷我会因此掉一两银子或少一两肉吗?
只要朱元璋父子不来寻他的麻烦,他便坚定不移地继续走这条败坏名声的路。
然而,令胡惟庸没想到的是,还没等他开口,一旁的解缙却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
“方兄,解某倒认为胡大人此举称不上离经叛道。”
“甚至,解某觉得胡大人这题出得还不够劲!”
一听解缙这话,胡惟庸顿时来了兴趣。
难得啊,乖乖,这还是他头一回听到有学子夸他出的题好。
“哟,大绅这是话中有深意啊,来来来,某听听你的高见!”
解缙并非胡闹,他一本正经地看着眼前二人,下巴微抬,神情傲然地说道:
“二位兄长,在解某看来,这科考若仅考四书五经,实在无法分出高下。”
“那不过是解某十岁前便能通读背诵的经义罢了。
光考这些,怎能显出咱的本事?”
“依解某之见,就该像胡大人这样,另辟蹊径出题。
虽略显怪异偏僻,但正因如此,才能显出真本事!”
“解某认为,科举本就不该让那些只会死读书的庸才侥幸上榜。”
“所以,解某觉得,胡大人只出一题,还不够!”
“若能再有其他考官出些史学、农学甚至杂学的考题,那才更妙!”
“不这样,怎能显出解某的过人之处?”
胡惟庸愣住了!
这莫非就是学霸的自信?
觉得考试难度不够,拉不开与那些学渣的差距,便要求老师出难题?
啧啧,真是狂啊。
不过解缙并非虚言,他是那种考一百只是因为卷面分只有一百的学生。
若给他一张满分一千的卷子,他才能真正施展拳脚。
胡惟庸深以为然,但方孝儒的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。
“大绅,你这话未免有些偏激了!”
“四书五经通读背诵又如何?方某年幼时也能做到。”
“越是读书,越觉得学问深不见底,岂是简单背诵就能掌握的?”
“依我看,与其让胡大人继续出那些离经叛道的怪题,不如在经义题上增加难度。”
“这样既符合儒家学子求学的正道,也能区分出真才实学与滥竽充数之人。”
胡惟庸没想到,方孝儒竟然也觉得题目不够难。
不过,方孝儒和解缙两人的优化方向却截然不同。
简单来说,方孝儒希望加深难度,范围不变,而解缙则希望扩大范围,难度无所谓。
联想到历史上对两人的评价,胡惟庸深以为然。
一个被称为铁头娃、书呆子,另一个则被称为广博学士,这外号确实贴切。
看着两人你来我往争论不休,胡惟庸笑眯眯地躲在一旁,觉得颇为有趣。